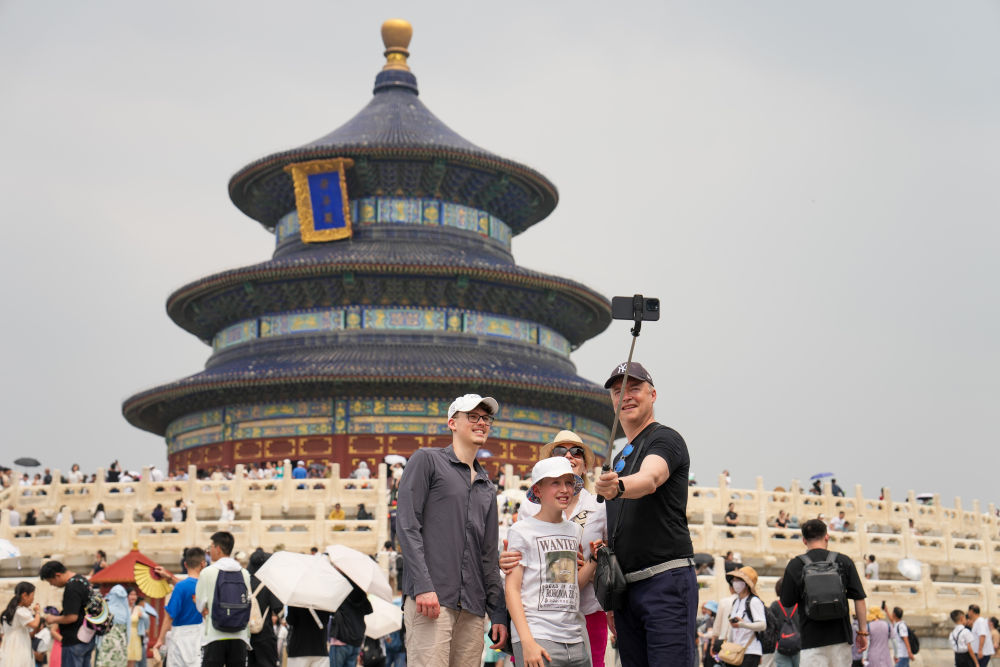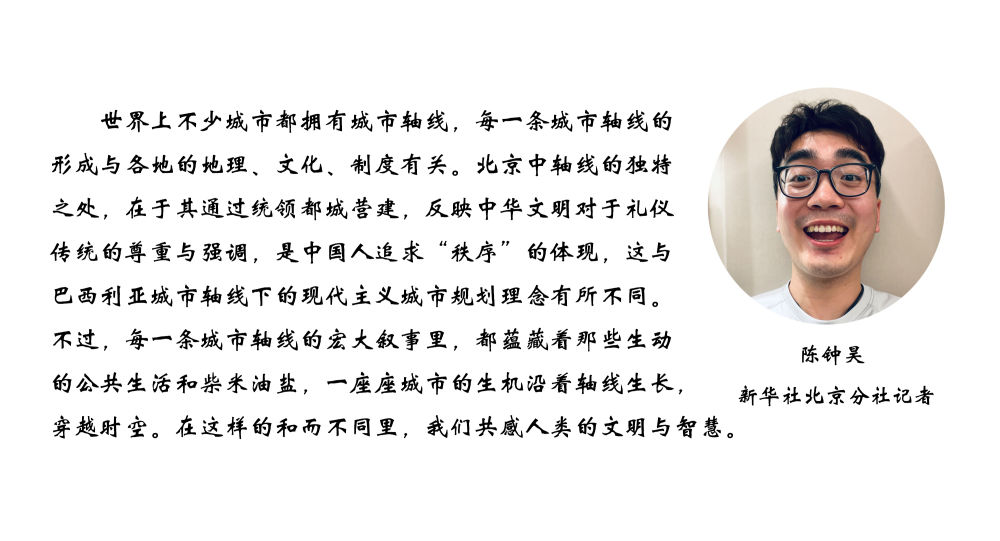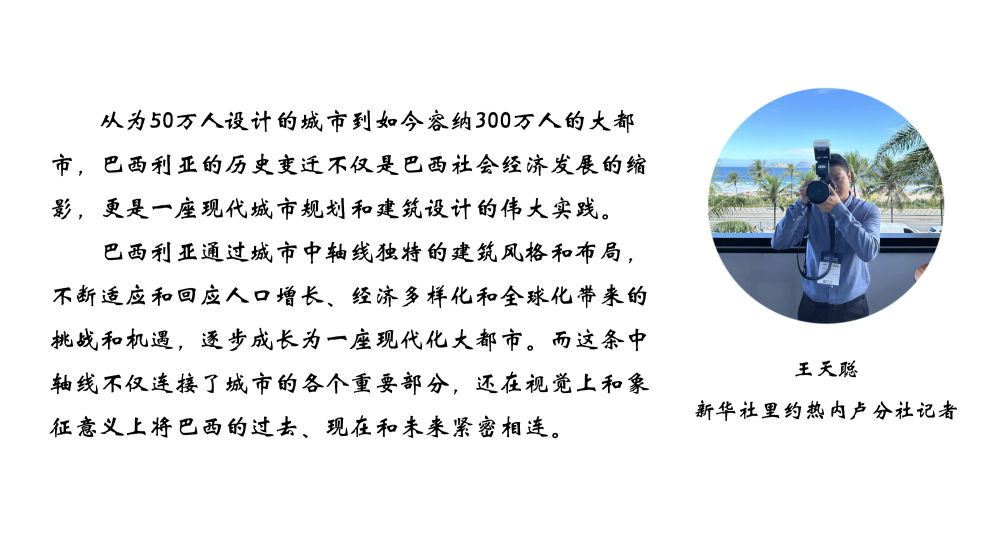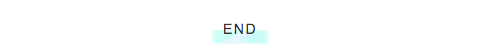新華社沈陽8月19日電(記者牛紀偉 王炳坤 強勇)舊日荒涼地,本日“魚米鄉”。
遼寧盤錦市和黑龍江墾區,兩片曾“荒涼”的地盤,現在演出滄桑劇變。
進進初秋,地處遼河三角洲的盤錦市迎來一年中最美季候;盤錦向北,西南年夜地另一端,黑龍江墾區行將迎來收獲。
新華社“新時期中國調研行”記者近期離開遼寧盤錦市和黑龍江墾區。這兩個已經的“南年夜荒”和“北年夜荒”,從亙古荒野變身“中華糧倉”的同時,高東西的品質成長不斷步,正在演出新的蝶變。
端牢中國飯碗:從鹽堿池沼地到“南北年夜倉”
北境沃野,天遼地闊。成片的莊稼像年夜海一樣看不到邊沿,微風拂過,稻菽千重浪,玉黍萬頃波。這里是中國最年夜墾區,4800多萬畝耕地上,農作物茁壯發展。
北緯48度線上,北年夜荒團體趙光農場無限公司的年夜豆地塊里,搭載著光譜成像裝備的無人機正在農田上空來去飛翔。十幾公里外的科技辦事中間內,技巧員郝思文坐在年夜屏幕前檢查田間實況記憶。他輕點鼠標,農田作物長勢、病蟲害等所有的信息便天生在一張圖上。
“以前種地看天,此刻種地看屏。”作為食糧生孩子“國度隊”,北年夜荒團體將聰明農業利用到食糧生孩子全流程。從這里往南1000多公里,聰明技巧也在遼河平原南端普及。在遼寧省盤錦市盤山縣承平街道高尺度農田示范區,種糧年夜戶郭凱輕點手機,稻田旁的閘門徐徐升起,汩汩清流便顛末溝渠流向田間。
“慧耕田”讓農區變得時興古代,但已經,荒漠、荒僻是兩個“年夜荒”的代稱,這里荊棘叢生、池沼密布,令人望而生畏。
70多年前,近百萬開荒者陸續離開“北年夜荒”,在戰天斗地中叫醒覺醒千年的黑地盤。現在,“北年夜荒”已建成我國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年夜型國有農場群,每年產出的商品糧可供給1.6億生齒。
進進新時期,黑龍江墾區和遼寧盤錦保持精緻化蒔植,特點化種養,正在古代農業途徑上走得更遠。
行走在盤錦鄉下,可以看見一包養塊塊水田外顯露白色塑料圍擋,景不雅奇特。細看會發明,塑料圍擋內別有洞天,一只只河蟹以水稻秧苗為蔭,潛藏在水中安閒徜徉。
“稻田養蟹很少應用農藥化肥,河蟹以水中的益蟲幼體和雜草為食,其糞便及殘餌又成了水稻的無機肥料……”盤錦市古代包養網化農業成長中間主任武強先容,今朝盤錦市“稻蟹共生”農田面積已到達93萬畝,恰是憑仗“一水多養、一地雙收”的“稻蟹共生”輪迴種養形式,品德精良的盤錦年夜米和盤錦河蟹作為“國度地輿標志維護產物”享譽全國。
躲糧于地、躲糧于技,也讓廣袤三江平原更好端牢“中國飯碗”。
展開農作物種源技巧攻關,衝破“洽商”題目;加速扶植一批合適耕耘、旱澇保收、高產穩產的古代化良田……2023年北年夜荒團體食糧總產量到達455.89億斤,完成“二十連豐”;農業科技進獻率高達77.1%,居世界搶先程度。
筑牢生態樊籬:從過度討取到反哺維護
有人說,盤錦是一座被悄悄放在濕地上的產業城市。
這座因油而興的產業城市,也因“濕”而美。擁有2165平方公里天然濕地,300余種珍稀鳥類棲息繁衍,人與天然在這里協調共生。
但曾有一段時光,這片濕地經過的事況過“掉地”的風險。從二十世紀五十年月起,數十萬青年離開這片“南年夜荒”,披星帶月揮汗開荒,開啟了油田開闢、治堿種稻的艱巨創業。
遼河油田出油了,鹽堿灘涂改進了,城市途徑平整了……可跟著時光推移,集約的產業生孩子讓河道變得混濁;一些葦田釀成稻田、灘涂釀成養殖場,過度討取讓濕地不勝重負。
若何守住濕地“性命線”?“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指明了標的目的。
2015年起,盤錦市打響生態恢復發令槍,任務組一一落實抵償轉產、異地置換計劃,到2020年完成遼河口濕地598個圍海養殖戶所有的加入,恢復濕地8.59萬畝、天然岸線15.77公里,培養了全國最年夜的“退養還濕”單體工程。
“就像一次刮骨療傷,固然很痛但值得。”盤錦市天然資本局干部孫弘願說,跟著一片片潮溝被清淤疏通,魚蝦開端洄游滋生,濕地的生態效能開端復蘇了。
與盤錦相似,顛末多年開墾,黑龍江墾區一度面對生態周遭的狀況相持不下:黑地盤水土流掉嚴重,濕空中積逐年遞加……北年夜荒團體建立新成長理念,采取工程、生物、農藝20項技巧辦法綜合施治,加大力度黑地盤維護。
穩住了生態修復的“基礎盤”,一批精雕細琢的環舉薦措正在兩地展開。
在北年夜荒團體扶植農場無限公司玉米地塊,一根根細弱的玉米翠綠挺立,輕風吹過,葉片摩擦收回沙沙響聲。北年夜荒團體扶植農場無限公司第四治理區主任齊利平易近用腳尖盤弄著地頭的黑土說:“你看這土多松軟,作物扎根好,滲水性也好。”
近年來,北年夜荒團體不竭深挖綠色產能,削減化肥用量,墾區各地紛紜施用無機肥替換化肥,停止糞肥還田。無機地塊不克不及應用農藥,就摸索出一套物理除草法,除輕率達90%。
“地力分歧,肥料配方也分歧。”在北年夜荒團體扶植農場無限公司,農業科技辦事中間主任趙新剛率領團隊,正給每塊地盤按方配肥。測土配方施肥可以有用防止過度用肥,近年來泥土板結情形獲得極年夜改良。
加大力度生物多樣性維護,盤錦濕地已是野活潑物棲息的“地獄”。
沿公路穿越蘆葦蕩,記者離開遼河口國度級天然維護區鶴類繁育維護站,技巧員趙仕偉正給十幾只丹頂鶴喂食,檢查小鶴長勢。
盤錦市采取種鶴豢養、人工繁育、雛鶴暫養、野化練習等方法,近些年共救助、繁育、放飛丹頂鶴200多只。盤錦市林濕局局長侯軍說:“作為遼河口濕地‘三寶’的丹頂鶴、黑嘴鷗和斑海豹,經監測種群多少數字均呈現增加勢頭包養網,鷗鶴紛飛見證了生態維護之效。”
做足游玩特點:從美不堪收到驚喜連連
時價寒假,盤錦紅海灘國度景致廊道游客如織。登上不雅景臺,向南看往是成片的紅海灘,回身再看,一幅宏大的稻田畫在風中搖曳,令人心曠神怡。
“景區內3萬畝紅海灘與陸地、蘆葦蕩組成了一幅奇美畫面,是可貴一見的河口濕地景不雅。”盤錦紅海灘游玩成長無限公司董事長孫煥新如許說。
取得“國際濕地城市”的稱號,盤錦市以紅灘綠葦、鶴舞鷗翔的生態之美,每年吸引近萬萬人次游客不雅光游玩。以濕地為brand,盤錦市不竭培養文旅新業態和花費新熱門。春季“不雅鳥賞花、踏青采摘”,夏日“休閑避暑、暢享田園”,春季“不雅紅灘綠葦、品蟹肥稻噴鼻”,夏季“嬉冰雪、泡溫泉、居民宿、過年夜年”,全時全季全域游玩急轉直下。
從遼河三角洲,到三江平原,奇特的天然景不雅吸引游客涌流。但盤錦市和北年夜荒團體的游玩開闢并沒有止步于天然景不雅。近年來,兩地不竭參加文明、體育、創意元素,讓外來游客從美不堪收中收獲驚喜連連,從而將“年夜流包養網價錢量”轉化成了“好口碑”。
黑龍江省西北邊境碧波萬頃的興凱湖畔,一座白色豐碑在北年夜荒開闢扶植留念館前巍然矗立,讓走近的游客不由心生敬意。
70多年前,百萬青年初戴瓜皮帽、啃著冷饅頭,在嚴寒荒野上戰天斗地的豪放,被留念館內一件件可貴文物、一幅幅汗青照片復原。
“‘自給自足、艱難創業、勇于開闢、甘于貢獻’的北年夜荒精力,已經鼓勵了幾代中國人。”北年夜荒團體總司理助理張如說,團體連續開闢軍墾文明,扶植白色教導、研學基地,不竭發掘北年夜荒精力的時期價值。僅曩昔兩年,北年夜荒開闢扶植留念館年觀賞人數就有20萬余人次。
既打“文明牌”,也唱“體育戲”。盤錦市每到秋夏季節舉行的“紅海灘國際馬拉松賽”和“冰凌穿越挑釁賽”,因擁有盡美的馬拉松賽道和中國最北海岸線的奇異冰凌,每年城市吸引浩繁跑友和極限活動喜好者前來體驗。
依托這兩個年夜型賽事,盤錦市舉行“最北海岸線露營年夜會”、逐夢冰凌越野賽、動力傘年夜賽、風帆拉力賽等運動,做年夜盤錦蘆花節、遼河濕地燈會等節會brand,周全晉陞“吃住行游購娛”辦事品德,吸引游客四時不竭。2024年上半年,全市招待游玩人數2716.8萬人次,同比增加64.5%;完成游玩支出195億元,同比增加13.3%。
這些天,北年夜荒團體閆家崗農場無限公司的“微不雅北年夜荒”農業樣板工程行將掃尾,園區內設有向日葵花海、稻作文包養化公園、康體氧吧等,將為市平易近供給新的農業游玩載體。
“年夜天然付與這里豐沃資本,我們將不負眾看、承前啟後,在守好‘中華年夜糧倉’同時,盡力為高東西的品質成長開闢新空間,開辟新景致。”閆家崗農場黨委副書記王鑫說。